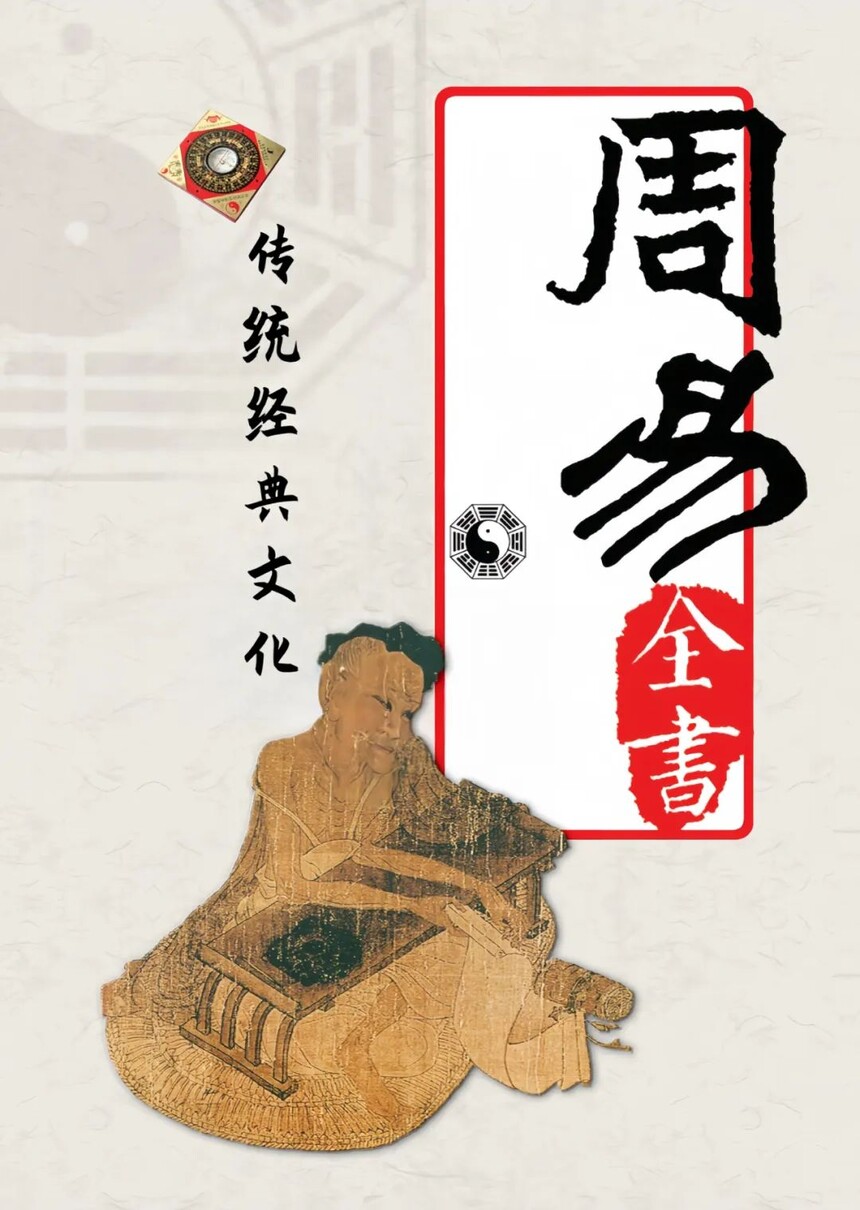|
|
《周易》的卦爻辞历史悠久,语言古老,因此常被认为难以理解。古今学者对其解释各有不同,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卦爻辞独特的“文体”。
因此,要深入理解卦爻辞的具体含义,必须掌握其“文体特征”。 笔者将《周易》中的卦爻辞的文体特征归纳为三点:象征性、押韵性和多义性,借此对卦爻辞进行符合原意的解读。 一、象征性 《周易》起源于占卜和筮法。 卜筮之书最显著的特点是“象征”这一文体特征。卦爻辞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,而是通过具体事物来传达某种象征意义。 正如古人所说:“《易经》是象征,通过事物的象征来揭示人事。” 理解这一特征后,《卦辞》中的一些难以理解的部分就会变得清晰。例如,中孚卦的卦辞“豚鱼,吉”,简洁明了,几乎没有文字解释上的问题,但阅读起来却令人困惑。 为何“豚鱼”能够被视为吉兆?古人认为中孚卦主要探讨的是诚信的问题,其中“孚”字意为“信”。“豚鱼”则代表小猪和小鱼,象征着民众,因此卦辞的含义在于统治者的诚信和对民众的恩惠。而现代学者则认为“豚鱼”是一种具体的生物,即河豚,认为“中孚豚鱼”指的是用弓箭射中漂浮在水面的河豚。这两种解释可以说截然不同。 如果我们深入理解《周易》的“象征性”特征,就能够找到令人信服的解答。在古代,豚和鱼常被视为人们互相赠送的礼物,象征着美好的祝愿。 在《论语》中,记载了鲁国权臣阳虎想要见孔子,于是送了一头小猪作为礼物(“归孔子豚”);而史书记载孔子的儿子出生时,鲁国国君送来了一条鲤鱼以示祝贺。因此,卦辞“豚鱼”提到这两样常见的礼品,象征着吉祥和美好,因此得出了“吉”的断语。 同样,坤卦的六五爻辞是:“黄裳,元吉。” “裳”是古代人穿在下半身的服装,通常与上衣搭配。它类似于现代的裙子,例如“黄裳”指的就是一条黄色的裙子。 可以想象,当一件色彩鲜艳、华丽奢华的衣服展现在眼前时,自然而然会让人感到一种吉祥和美好的氛围,因此断辞便说:“元吉。” “元吉”意味着非常吉利,这类卦辞在《周易》中常有体现,无需过于深入探求。 二、押韵性 《周易》中的卦爻辞有不少是韵文,但由于古今语音的差异,用普通话朗读时已经无法体现出韵律。 震卦的卦辞中提到:“震动来临时,令人感到惧怕,言语变得沉默;震动的声音传遍百里,依然不会失去佳品。” 在《周易》时期,虩、哑、鬯这三个字是有韵律的。 例如,中孚卦的九二爻辞中提到:“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;我有好爵,吾与尔靡之。”这里的“和”和“靡”在上古音中也是押韵的。掌握卦爻辞的押韵特点,首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断句。以坤卦六二爻辞为例,通常可以理解为:“直方大,不习,无不利。” 古人认为这是在阐述坤卦象征的大地具备正直、方正、广大三种美德。然而,也有人从押韵的角度提出异议,指出如果仔细分析坤卦的六条爻辞,如“履霜”、“直方”、“含章”、“括囊”、“黄裳”、“玄黄”,都能够形成押韵的效果。 因此,只有在将“直方”进行断句时,把“大”断在下方,才能理解爻辞的本义。 根据这一点,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。关于讼卦中的九二爻辞,古人解释说:“无法胜诉,回到自己的家乡,逃避而不受惩罚,人数三百户,没有过失。” “逋”表示逃离,“眚”则指代灾难。 这种解读的意思是,如果一位贵族在官司中败诉后逃回自己的城镇,而这个城镇的人口仅有三百户,人数不算多,未对对方构成威胁,那么就不会遭遇灾难。 “无眚”的条件是“三百户”,这个表述显得有些曲折。如果考虑到押韵情况,“逋”和“户”这两个字的古音是押韵的,所以应当以“逋”字为断句。整句话可以读作:“不克讼,归而逋,其邑人三百户,无眚。” 某位贵族在打官司时失败,逃回了自己的城镇,而他的罪责只在自己一人身上,导致该城镇的三百户百姓并没有受到灾祸。这样表述更为流畅。 其次,押韵的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卦爻辞中的“变文协韵”现象。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就曾针对《周易》的变文协韵提出一个典型例子。他注意到小畜卦上九爻辞中的“既雨既处”,因此指出:“处者,止也……意指雨的停止。不说‘既雨既止’,而用‘既雨既处’,这是为了使变文与韵律相协调。” 这句话的“处”实际上是“止”的意思,不过爻辞并没有使用“止”这个词,而是选择了“处”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前面的“雨”字押韵。除了俞樾提到的通过更换字词的“变文”类型外,我们还发现通过调整语序和增减字词来实现押韵的两种方式。调整语序的例子可以参考离卦九三的爻辞:“日落时分的离,不敲缶而唱歌,那就会引发大年纪者的叹息,结果将是凶险的。” 这是用太阳西斜时的余晖来比喻人到老年时,应当享受生活,否则最终只会感到后悔。 根据文意,“大耋之嗟”应理解为“大耋嗟之”。之所以写作“之嗟”,是因为“嗟”与“离”、“歌”的上古音能够押韵——通过改变文字来使韵律协调,可以增加或减少字词的类型,例如在《周易》旅卦六二爻辞中提到:“旅即次,怀其资。” 九四的爻辞是:“在旅途中,获得了所需的工具。”而巽卦的上九爻辞则是:“在床下的巽,失去了其工具。” 在“资”字后面加一个“斧”字,或者说把“资斧”中的“斧”去掉,目的是为了保持押韵。“资”与“次”可以押韵,而“处”、“下”、“斧”的上古音也能够产生韵律感。 由此可以推断,"资"和"斧"是并列关系。这里的"资"指的是财物,而"斧"并不是指砍伐的工具,而是古代的一种货币,已有相关的考古实物作为证据。因此,将“资斧”解释为“所资之斧”或“利斧”的说法值得商榷。 三、多义性 这里的多义性指的是在同一卦中,同一个字常常具有不同的含义。 《周易》的卦爻辞具有另一个重要特点,但古代经学家几乎没有注意到,甚至进行了牵强的解释,直到现代学者才对此有所揭示。 李镜池提到,明夷卦中反复出现的“明夷”二字,可以解读为“鸣鴺”,也可以表示太阳落山的意思,或作为地名,或作为弓的名称。而井卦中的“井”字,则有井田、饮水井和陷阱这三种含义(《周易探源》)。 李氏的具体观点可能值得商榷,但关于“一字多义”的论述确实值得关注。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,再挖掘几个例子,以供读者参考。 革卦中的“革”字被普遍解读为变革的象征,古人对此有较为一致的看法。在爻辞中,确实可以找到几处“革”字表示变革的意思,比如“巳日乃革”和“小人革面”。然而,初爻中的“黄牛之革”则明确指向“皮革”的含义,这正是典型的“一字多义”现象。 古人也不得不承认“黄牛之革”代表了皮革的意义,但他们仍然费尽心思将其与“变革”联系起来。正如王弼所说:“牛之革,坚固而不可改变。” 再来看贲卦,这个卦的六条爻辞中各自都包含一个“贲”字。“贲”的古义是指“文采”与“光彩”,例如在《诗经·白驹》中提到的“贲然来思”,“贲然”表达了光辉的样子。作为动词时,它有“装饰”的意思。在贲卦中,初爻的“贲其趾”、二爻的“贲其须”和五爻的“贲于丘园”中的“贲”,都表示对脚、胡须和家园的装饰。而其他三个爻辞中的“贲”字则需要谨慎解读。 三爻“贲如濡如”中的“贲”,应理解为光彩的样子,与“濡如”所表达的润泽之态并列。与此同时,“贲”也有白的含义,四爻“贲如皤如”和上爻“白贲”同样取白的意思,与文中的“皤”“白”相互关联,突显出洁白的特征。这样解读,使得词义更加通顺。 比如涣卦,爻辞中有七个“涣”字,古人通常将“涣”解释为“离散”,这七个“涣”字的意思也都被理解为“离散”。其实,除了第四爻的“涣其群”可以符合这个解释(即解散其群体)以外,其余的解释都显得不太通顺。 我们认为,二爻的“涣奔其机”和五爻的“涣王居”中的“涣”与“焕”是相通的,均含有装饰的意思。其中,“奔”可以与“贲”互通,和“焕”有相同的意义,依然属于装饰的概念。这两句爻辞分别指的是对案几(机)和君王住所的装饰。 三爻中的“涣其躬”和上爻中的“涣其血”中的“涣”,与“浣”字相通,表示洗涤的意思,分别指身体的清洗和血迹的清除。而五爻的“涣其汗”(根据马王堆帛书乙正)中的“涣”则应理解为发散的含义,意指汗水从皮肤中蒸发出来。通过不同字义的理解,能够更清晰地表达意思,避免了生硬和牵强的解释。 《周易》确实不易理解,尤其要避免故意牵强附会。只有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,紧扣其文体特点,广泛听取不同观点,同时坚持有理有据,才能真正领悟《周易》的核心思想。 |